
近日,浙江人民出版社“何以中国”书系推出力作《何谓唐代: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》,该书整合日本学界最新研究成果,突破“唐宋变革论”,超越“征服王朝论”,呈现理解唐朝的新视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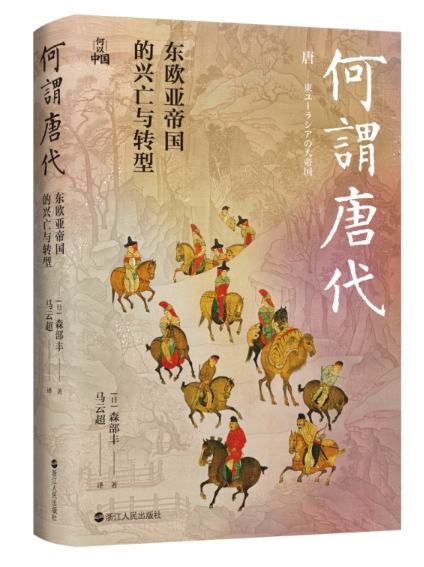
《何谓唐代: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》以广阔的东欧亚世界为舞台,全面介绍世界性帝国唐朝二百九十年的历史。起于隋末的唐朝,在十数年间陆续平定群雄割据,并攻灭东突厥,唐朝皇帝被尊为“天可汗”,建立起统治农耕、游牧、绿洲等文明,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帝国。此后不断扩展,臻于至盛,至“安史之乱”急转直下,开始走上漫长的转型之路。
作者森部丰教授专攻粟特人研究,在现有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,他从粟特人的迁徙、定居、建立势力,参与并融入唐朝政治军事活动着手,剖析了唐朝不同于既往朝代,能够兼收并蓄、开放包容的侧面,以及伴随体制变迁经历的历史性转型,展现出一幅全新的唐代历史面貌。
作者简介
〔日〕森部丰,1967年生于爱知县,专攻唐五代史、东欧亚史。现为关西大学教授、中国唐史学会海外会员。
译者简介
马云超,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,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,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中日关系史、东亚海域交流史。
内容试读
“贞观之治”与明君太宗的真相
李世民将玄武门之变中追随自己的功臣安排在政权的中枢位置,基础得以巩固后才继承皇位,庙号太宗(626~649年在位)。他或许还是感到内疚,所以避开宫城正殿的太极殿,选择在东宫的显德殿即位。早在秦王时期,太宗就设置包括后来成为宰相的房玄龄、杜如晦等“秦府十八学士”作为顾问。成为皇帝后,他还遴选南朝系统的文学之士作为弘文馆学士,令他们轮流值宿,在政务闲暇时进入内殿,一同探讨古代圣人的言行以及政务的善恶优劣。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后第二年的正月,太宗改元“贞观”(627~649)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贞观之治”的开端。
太宗的治世持续了二十三年,而世间所说“贞观之治”是从最后的抵抗势力梁师都被平定,国内重新迎来和平时代算起的(628年)。从那以后,唐朝可以说真正开始统治中国。
关于贞观初年的情况,《新唐书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当年(630),一斗米是四到五钱(一枚‘开元通宝’是一钱),家家户户不用锁门,牛马数量日益增长,旅客不必自己携带粮食。在这样的太平盛世下,一年间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。”
在治世的第四年就出现这样的盛况,史料上的记载或许有些夸张。但太宗的治世中确实存在过这样的情况,这对于形成“贞观之治”印象的作用是无法否定的。
太宗之所以被称为明君,不只是因为他给天下带来太平盛世,也是因为他善于用人,能够听取臣下的劝谏,其间的代表就是魏徵。魏徵原本跟随隋末群雄之一的李密,降唐后又辅佐李建成。当时,魏微曾向李建成进言“早除秦王(李世民)”。玄武门之变后,太宗召来魏徵问道:“你为何要挑拨我们兄弟?”魏徵回答:“若皇太子早听我言,必不会有今日之祸。”经过这番问答,太宗开始重视魏徵的才能,不断提拔他。
归附太宗后,魏徵的直谏多达二百余次。对于其他臣下的谏言和意见,太宗也都能虚心听取。拥有坦率进言的臣子,施行光明磊落的政治,这是太宗的特点,也是他成为明君的原因。作为此前中国王朝中从未有过的全新风格的皇帝,太宗经常会与臣下进行政治问答,其间的内容在玄宗时期得到整理,那就是《贞观政要》。
太宗虚心听取臣下意见的态度称为“兼听”,这是贯穿《贞观政要》的主题。“兼听”是作为隋炀帝不听意见,导致国家灭亡的反题(Antithesis)而出现的,可以理解为创造出与“昏君炀帝”截然相反的“明君太宗”的形象。实际上,太宗的兼听也有表演性质的一面。贞观中期,魏徵曾对太宗说:“陛下在贞观之初鼓励臣下谏言,并且能高兴地接受。如今却不同了,虽然努力想要听从谏言,但还是会面露不悦。”在唐史学者的概说中,太宗即便如此仍能自我反省,依然称得上是大器,不过也有学者作出辛辣的评价:“太宗是带着几分自卑的知识分子型的君主。”(三田村泰助,1963年)
——摘自《何谓唐代: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》第一章 朝着东欧亚帝国飞翔
来源:南方网